1989年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

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是高考和参军入伍,城里的待业青年可以接班或招工进厂成为工人,在当时的年代,机关事业单位人员、教师、医生、工人工资标准是差不多的,企业工人奖金、福利待遇还好过机关事业单位。
1982年前后,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大约人均一亩半地,大人孩子一年四季都要参加劳动,机械化程度低,农业生产几乎全靠人力,农作物产量却不是太高,交农业税外,还有三提五统,辛苦一年剩不了多少钱。
农村的孩子,都要参加劳动,割草、放羊、喂猪、饲养家禽,主要是养殖大了卖钱,鸡下了蛋,也舍不得吃,要拿到集市上卖钱,孩子们读书学费,衣服、鞋子,柴米油盐,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柴油都指望着它呢。
十几岁的孩子,就是个半大劳力了,犁地、打畦埂,栽红芋、翻秧、刨红芋、晒红芋干,给小麦追肥、浇水。割、捆、运送回家,晾晒、打场、堆垛,过个麦季脱层皮。棉花打营养钵,育苗、移栽、打杈、追肥、浇水、打药、拾棉花、晒棉花,拉着板车去棉站排队卖棉花,割豆子、掰玉米、摘绿豆,总是有干不完的活,如果考不上大学,一辈子就得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。
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,考上大学、哪怕是中专,都能转为城镇户口,成为吃商品粮的“公家人”。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,在人们的心中有很高的地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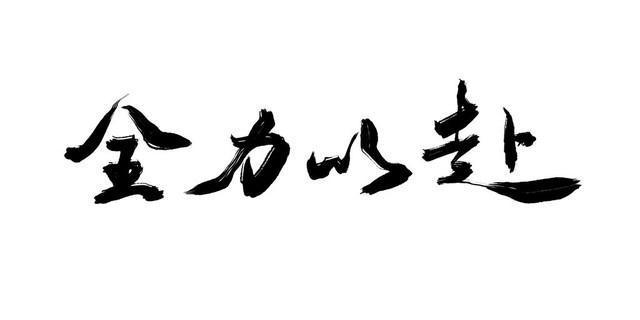
我1988年参加预考时就落榜了,没有资格参加高考,回到家里,感到十分落寞,十多年的学习,以失败告终,成绩不在班级中等以上的就没信心复读了。
1989年我复读一年,成绩稳步上升,从开始的班级50多名,到预考时已跃入班级前5名,预考后,全班70人只通过了14人。七月七、八、九是全国高考时间,我们的考场在县一中,我一举取得了班级第二名的好绩,第一名505分,我第二名497分,江苏省文科二本分数线是495分,全班考上本科、大专、中专的共6人。
后来,我录取了省内一所财经类大专学校,三年后毕业,分配到县直某单位工作,至今已33年了,再过几年也该退休了。